描述
內容簡介
在生死面前,世人做何姿態?高僧又做何姿態?
淨土祖師蓮池大師恒於案前,書「生死事大」以自警醒──無常迅速,當勤精進。的確,死亡是每個人不可避免的功課。
這本書,即是一本關於禪者們臨終之際,面向死亡的「告別、辭世」之話語、詩偈,敷演而就的作品。
作者梁寒衣,以她的學佛修禪和辭藻文采雙重素養,寫出了禪門祖師的修行路程,帶領讀者領略這些禪者參透生命實相後的豁達,用他們所作的詞偈和開示,演繹出佛門高僧行走人間的步伐,竟是如此的莊嚴與美麗!示現於世間的相狀竟可以這樣的多情與超脫!
多采多姿的行者風範、令人仰望的修行身影、行願甚深的包容與氣勢、無比的深化與細行,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樣,各自閃燿著獨自光芒,同時交織成一片美麗的夜空。
目錄
推薦序 待汝來證耳/林谷芳
自序 花開最末
第一篇 何必喧動如斯?
第二篇 鐵橛開花不待春—死亡,如鐵棒子忽然開滿了繁花
第三篇 無偈便死不得嗎?
第四篇 白鳥湮沒,秋水連天
第五篇 行腳去!—道在用處,用在死處
第六篇 我是快活烈漢
第七篇 瘋癲漢子照過來!
第八篇 當慧日昇起•之一—日輪午后見全身
第九篇 當慧日昇起•之二—臘月卅十到來
第十篇 生、死,夢的如一
第十一篇 不妨留髮候燃燈
第十二篇 大音希聲
第十三篇 松風澗雪•紅爐優缽—五十三歲的死亡
第十四篇 火光三昧
第十五篇 孤輪獨照須彌峯
作者簡介
梁寒衣,臺大外文系畢。曾參與高棉、越南的難民救援工作;異域目睹的生存死亡觸發了她人道思考的寫作動機。
出生禪門,以直了生死為本務。修持因以禪門為髓腦,以華嚴瀚海為終極。
蟄隱山茨十數載,參究《阿含》、《楞嚴》、《維摩詰》、《華嚴》、《大涅槃》等南、 北傳教典諸部。1999年開始,陸續於寺院、講堂、禪學中心,弘講《勝鬘經》、《六祖壇經》、《佛祖道影》、《證道歌》等諸部,並擔任文學與禪學指導。
曾獲1989年「聯合文學」小說中篇推薦獎。1996年「普門文學」短篇小說獎。著有 《上卡拉OK的驢子》、《赫!我是一條龍》、《黑夜裡不斷抽長的犬齒》、 《一個年輕的死》、《將名字寫于水上》、《雪色青缽》、《水仙的炎鏡》、《迦陵之音》、《無涯歌》、《優曇之花》、《丈六金身,草一莖》、《我們體內的提婆達多》、《聽啊,緬甸的豎琴!》等。
特別推薦
待汝來證耳
文/林谷芳
禪,直捷一句,就在「了生死」。
這生死,無所躲閃。生之已在,只能領受;死之而來,也只能撒手。販夫走卒、帝王將相、倜儻風流、干雲豪氣,在此皆同,一樣都只是個:「不由自主」。這不由自主,尋常人避談,大丈夫轉彎。一句「未知生,焉知死」,肯定現世,卻對現世的結束避言。宗教修行不然,它直扣生死,是「未知死,焉知生」之事。但可惜,繁衍既多,原點竟常模糊,絕大多數人甚且就以之為現世福報之所依。禪不然,對生死之事,它歷來何只毫不躲閃,更就直搗黃龍。而生既已矣,死,就印證、就示現,乃成宗門之絕地風光。
諸家中,禪者之辭世形貌最為廣垠。或大美、或莊嚴、或平常、或遊戲、或不可思議,卻皆以死為尋常映現之事。而由此,你方知面對此生命之天塹,人,竟可有如此多樣、如此自在之選擇。諸家中,禪者之辭世形貌最為親切。因在此雖超乎常情,卻非他方世界之事。相較於宗門,密教行者之辭世尤多有神異,但就因其神異,在世人眼中反如神話,於生命現前之觸動乃常不深。己身之自證,是宗門之基點,在此原點相互惕勵勘驗,遂成道人彼此之互證。就如妙普庵主欲辭世,要修書予雪竇持,而雪竇兩年後方至,妙普庵主竟就延壽兩年,待雪竇一來,見其尚存,乃作偈嘲之,說他「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而面對此,妙普的一句則是:待兄來證明耳!
這「待汝來證」是宗門行儀最精彩的一章。在此,有時是道人互證,如龐居士一家的坐脫立亡;有時是道人對學人的示現,如洞山示寂,儼然坐化,弟子號慟,他遂開目復返並令主事辦愚癡齋,說法後再亡。而示現時,有人是劇情張力十足的印證,如隱峰的倒立而亡,衣袂不墜;有人是平常的就此而行,如布衲如因友題詩,以其「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他遂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之因緣,竟就現前即行地辭世而為古人。可無論互參、示現,無論驚世、平常,這裡既絲毫無有躲閃,乃盡現禪者的極致風光。的確,禪,兩刃相交,無所躲閃,這死生決絕的現前一刻,正乃生命最箭鋒相拄的一刻。要談懸崖撒手,要談電光石火,這就是最真實、最嚴厲的勘驗,而既沒有再次之機,對人、對己遂皆無以相瞞。正如此,寒衣在此書乃以行者之姿取此禪家臨終現前之偈,為世人活生生再現祖師身影。原來,事之記於禪籍,已令人欣羨,引人遙思。而在此,祖師身影更就如在身邊,你也已如親臨現場印證的行者。
身為行者,能親臨現場,誠乃生命之大幸;未能親臨現場,也幸有寒衣此書而為的再現!但無論是否親臨現場,身為行者,卻總得體會祖師之示現,並不只在藉眾人之見以證自己之真,更深地,他還要學人因此觸動,有日也能成為自證的道人。寒衣此書,雖非自身死生之書寫,但這祖師對己身自證之真切觀照,對學人他日之證之悲心期許,卻正是貫穿全書的。而之所以請我為序,想必也在藉此因緣,邀我--「待汝來證耳」!
花開最末
這條路雖然人跡罕至,卻也是一條正真之道。
當我提出要寫一部《辭世偈》,一部關于禪者臨終之際,面向死亡的「告別、辭世」之話語、詩偈的作品,「怪人。」朋友道:「你真奇怪,也真可怕!沒有人會買這樣的書,讀著各種死亡、告別之語罷?」他建議道:「你為什麼不寫開悟詩呢?像別人一樣,『悟道』的詩偈,赤坦、光明、活潑、鮮耀,且是充滿希望的開始與突破,人人都喜歡。」
是啊,裂破乾坤,獨耀全真的「悟道偈」,如嬰兒的初生一般,出生出炯絕孤樹,獨 超宇宙、器世的「沙門一隻眼」,粉碎了累世積劫舊有的框架、思惟、與皮殼,的確是視象嶄新、關鍵、決定且霹靂雷霆的一刻:
唯因行者的確經驗了不可思議,無以言說、也無從指涉的剎那:一個徹底的撞擊與粉碎:宇宙、器世瞬息銷為煙塵,「我」與「我的心識」頓時夷為齎粉、化為烏有,即連佛家所指證歷歷、收藏記憶、意識種子的「阿賴耶識庫」也殞為幻翳,人與我;佛與魔;眾生與世界;物質與精神;此世與彼世,統統淪為幻構。
是啊,悟道!一個禪者終其一生削筋剉骨、汲汲苦行,汲汲參思、汲汲研磨,所冀望抵達,卻窮一生、二生、三生乃至十生、百生,也未必能保證經驗的偉大片刻,而「悟道偈」正是經驗了此旋乾轉坤、不可思議的「翻轉」與片刻的人,所直出心目,直揭、直撥、直指的「感言」,自然是光燦、奪目,能使人仰首、翹目、期許期待的。因為它宣示的是一名嬰兒的誕生。一雙初張、初開的明亮眼目。且剎那所見,與諸佛、菩薩、祖師、古德無二無別。就在這一刻!
此處,必須有個更嚴格嚴謹的定義,這個「辭世偈」必須是死亡的當下、現場發出,不能是「預設」而來,不能是死亡前的二日、三日、一週、數月、乃至半年、一年,預先提筆研墨,窮詰文思文采,「事先構設、模擬」而來,已算準了留下一段「高僧的身影」,一尊崇高、偉岸、光華四射或俊潔完美的形像,留給後世去仰望、朗讀、憑弔。雖然,這種「預作伏筆」的辭世偈,多少也能呈現一名行者之於死亡的態度以及「之於自我的身影的觀點與期許」,也不失為行者的心跡與感懷。但總嫌跡痕太過,是「打造」、「形塑」出的「辭世之花」,且預先擱凍了太久!莫若磊朗朗、真切切,臨行之時,淋漓歌吟出的親切、感動:因為,它才是當前當下開出的迸放活躍、香息湧烈的鮮花,剎然開放、猝然殞滅,卻出自肺腑、幡然明亮。足以截斷時空,定格禪者的真顏與本色:唯因,那樣的開花方式,才是本色天然的!也才是「傾生命活於眼前的一瞬」。
悟道偈,是起點;辭世偈,是終局。之於一名禪行者,悟道,恰若視線敞闊,明見照了,握有實際行道的路標與藍圖。辭世偈,卻是行者孤身上路,踅歷道路重重的關隘、險難、蒼涼、寂寞,幾回生死,幾番魔考後,站立的盡頭與終點:那人如此回眸,以寥寥的數語,總結了「向所來處」的蕭瑟與曠渺,修證與經驗。是結語,一個從起點至終點所劃出的「一圓相」。 如此,悟道偈,是道路起跑的槍聲,霹靂雷振,撼人心神。辭世偈,卻是道途玄寂處,面向明月的通身一躍。明月現不現前,則看悟道者於道路途程中保任、修證的工夫了。僅看悟道偈,而不了辭世偈,則無異只是讀了「上半聯」,至於「下半聯」畢竟如何,就只能是虛線的圓弧,僅能「模擬想像」了。
歷來「文人禪」、「文字禪」往往由於缺乏實際參禪的經驗,也缺乏實證實修的系統,常常將「悟道」與「證道」混為一談,所耽嗜玩味的也通常是輝煌炯耀的悟道詩、偈;書寫者如此,閱讀者亦然,統統於門外觀禪、說禪,也多半誤以為悟道即是證道:大家錦心繡口,你一言、我一語的唇槍舌劍,搬弄現成的套語、公案、佛典、名句,尖舌快語、玲瓏剔透、機鋒不讓、痛快揮灑,便以為是悟了、「明心見性」了。參禪、修證若是如此這般地容易,如此閑情逸致、口角生風,則歷來祖師、古德,住茅蓬、下死工夫、苦工夫的,定然是舉世最下等、最最鈍根、愚闇的人。
悟道偈,人人已揭過、舉過太多,那麼,即讓山行者無忌無諱地來一段辭世偈罷。黃昏向晚,長鋏歸去,一名學習者總需要在前輩的死亡、辭世中,透曉自身的死亡與辭世,以之為座標、為明鏡。
唯因,僅瞭望見明月的初昇,是不夠的。「末後偈」始是明月的落入眼前,翻身疊合。
書摘
試閱一
「何必喧動如斯?」
「曹洞」祖師洞山良价的「愚癡齋」是給予愚盲凡夫的警世之鐘─洞山良价示寂之日,剃淨鬚髮,披搭上祖衣,令僧人擊鐘,便如此端儼而逝。大眾悲慟哭號,哀哭喧天。
師即睜開眼,寧寂、平和地道:「出家兒,心不附物,始是真修行。有何可悲、可戀的 ?」於是命令主事僧,籌辦「愚癡齋」,與大眾齋後再行訣別。負責的僧眾慕師、敬師、崇師、仰師,依戀不捨,自然,這場「愚癡齋」拖拖拉拉,辦得心不甘、情不願,充分發 揮了「老牛拖車」的牛步,張羅到了第七日,菓品、食材、齋筵始才備妥。洞山良价也便陪著大眾進食了一點,跋涉了這整日整場、特為「愚癡者」而設,且也充滿了告別情緒的「愚癡齋」。許是個冗長,而難掩悲戀的場景,齋宴結束,到了夜裡,作別道:「僧家何太麤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第八日,使人備好湯浴。沐浴了,即端坐長逝。時年六十二歲。要生,即生;想死,即死,去來自如,縱橫三千。洞山良价如實坐證了一名峯頂的禪者無掛無礙、瀟灑逸脫的風貌。
沸騰焦煎,惶急紛亂於「死之過程」:插管、氣切、電擊……無所不為!遂行種種極 致極限的醫療手段、醫療科技,而使臨終者倍受剝削,在未死之前早已提前領受煉獄的種種痛切、非人的虐拷、摧折,與凌遲。即若此強勢、鐵腕、極限的醫療,果然成功地延續了病者幾日、幾週、幾月,乃至數年的生命,通常所延續的,也僅是蝕奪而盡,風燭一般 ,痛苦羸殆的殘軀:飽經煉獄庖烙整治,又踅返回來,面向另一群﹁以愛為名﹂,而遂行了極致挽留的親眷們。彼此一樣跨躍、也經受了身內、身外、肉身與精神層次的樣樣地獄鐵圍,苦刑、創痛。
極端、極限的醫技醫療,使得「葉落歸根」般自然、安適、安寧的死亡愈來愈難、愈來愈顯遙不可及……乍看彷彿尖端、文明的科技所致,究其本質卻源於世間的「戀生惡 死」,醫者、病者,及病人的親眷俱然。正由於盲目的愛染生死、戀執生死,所以始以同樣盲動的激情、拚盡一切、使盡所有,奔竄激走,意圖定格住「肉身的存在」,且也不停下來返問一下:這延續的一口氣究底是為了什麼?目的、意義何在?一具肉殼子,呼吸不中斷,便就是「生」了嗎?
試閱二
「無偈便不得死嗎?」
「無偈便死不得也!」,南宋叱咤風雲的臨濟高僧大慧宗杲如是喝。宗門道「同生不同 死」─意思是,見性、悟道,所見、所悟,決無有二,定是此不異的法身、法性。一切禪者莫不皆從「毘遮遮那頂門中生」,若還有旁生,則定是見鬼。生則固然同生,同一達摩鼻孔中出氣;死則未必同死:禪師們的才具、性情、風格、志趣……,千差百異、琳瑯萬態,其接引行人、施設門庭,痛下鉗錘的相狀,如是,也炯絕孤異,波濤萬頃、變化莫測
由是,同是宗下禪人,有人愛開「真金鋪」,有人則偏偏非開「雜貨鋪」不可:大悲所至 ,即使來的人索求的只是ㄧ粒老鼠屎,這個「悲魔所使」的禪姥姥也便這般硬生生自老古的抽屜中拈拾一粒給他;換另一個石磨一般的急性鐵禪和則可能劈手即拗折斷那人的胳膊,更別提什麼拈不拈老鼠屎了。
此中,沒有商榷地!活時,風格萬千,死時,自然也各異其趣。平日,修法、示法,氣質、顏貌,已然如斯「同生不同死」,到了大限來臨、真死之際,自然,也「各自論述 ,百花競豔」─有的亢烈、有的嫵媚、有的風神瀟灑、澄泞安恬,有的詼諧幽默、突梯古怪、有的詩化詩情、靈氣懾人、有的氣魄慷慨,直如武士斷首,更有的一默謙沖,以無聲之聲,使得須彌也為之傾倒。
湛堂遷化,大慧時年二十七歲,爾後九年間,大慧徧遊於洪覺範、潛菴源、兜率照、海會從、草堂、靈源……等諸叢林巨德座下,由於俊材神敏,以及某種累世恍然的宿慧,而遊走無礙、機辯縱橫,莫不受諸禪德的首肯。同時,與著名的居士張無盡、韓子蒼從遊深密 。世、出世間,一時名德,宛如繁花璀璨,同聲墜入他的袋口中般。
三十六歲,得知圜悟克勤奉詔將移駐天寧。不忘湛堂遺訓,大慧準備預先前往天寧寺等候圜悟的抵達,同時,立誓道:「將以九個夏日為期,此人的禪若不異諸方,仍妄自肯我、以我為是。我便去寫『無禪論』。再無須為參禪一事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了。莫如好好弘講一經一論,把本修行,至少後世再來仍不失為佛法中人─」於是,典購了一部清涼澄觀所註的《華嚴疏鈔》先抵天寧寺。
驚濤裂岸走過智覺、而偉烈的一生,公元一一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夜間,有大星墜落於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大慧聆聞,微笑道:「我將行去。」八月初九薄暮,徒眾們意識到大慧已無意人世,乃簇擁於寢室間,大慧以手搖曳道:「我次日才走。」第二日五鼓聲響,大慧書寫完遺奏,咐囑了法嗣,徒眾們請他留下「示寂偈」,大慧便厲聲喝斥道:「無偈便死不得嚒?」一個逆反時流,逆反到連辭世偈也懶得留下的人─連惺惺作態,捏塑文句,以便留下一介高僧永恆的圖像、臨去的姿影,也懶得的人。
相反地,卻像個暴烈的老頭兒一般的喝叫。要徒眾門死了這般想留什麼「辭世偈」、依此證據出什麼高僧的「偷心」。於他而言,都只是眼底、根骨裡捏出的虛怪。都僅是世俗心不去,聲名心不捨,三界牢籠的鐵框子。此正是參禪要破的「生死心」啊!由是,此佬要骨楞楞的厲聲反問:「無偈便死不了嚒?」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什麼熱大?
─然而,大眾是鐵了心,非索求到辭世偈無以定心。拗不過此切切哀懇,臨終的大慧提筆一揮而就,書罷,即投筆就寢,吉祥而逝。這是他最后的慈憫,也是他最後的破。
試閱三
「我是快活烈漢」
宋朝嘉興府性空妙普庵主,久依於死心禪師座下,獲得印可,結茅庵於青龍野,恆常吹著一支鐵笛,蕭散自娛。宋高宗建炎年間,逆賊徐明叛亂,道經烏鎮,肆行屠戮,血淤溝壑。妙普庵主為叛賊所擄。賊人暴怒,欲斬殺他。性空妙普道:「大丈夫要頭,便斫取 。何須暴怒?我死必然,可否祭一祭我呢?」他要求「活祭」,且說得如許安恬泰然、輕鬆自若。反賊於是奉上葷羶肉食。「誰能為文祭我呢?」妙普庵主又道。既索「祭品」,又索「祭文」,熱鬧不休、花樣不少,反賊忍不住大笑,便索性奉紙筆給他,看看此人還能變啥玩意出來。妙普縱筆大書,詞旨豪邁超達。書畢,舉箸大吃大喝,而後,停筷笑道 :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吟罷,大喝:「斬!斬 !」賊人凜然大駭,羅列而拜,護衛他出營。烏鎮,因而免去更多的焚殺屠掠、烽火浩 劫。遊戲生死,縱橫?跳,如魚戲碧波。這箇「快活烈漢」的末後句 ( 這個詞,當然, 於宗門中有更深的意義,是須深深參的) 是這樣的─於生命的最終─那個冬日,他造了一 座巨大的大盆。如同現代浴缸的構造,底下鑿了一個孔洞,置了塞子。造好,書信給知交雪竇持禪師道:「吾將水葬矣。」過了新歲,雪竇持訪謁,見他仍活著,作偈嘲笑他道:「咄哉老性空!剛要餵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笑他婆婆媽媽,要去不去,何必囉哩叭嗦。性空閱偈大笑道:「便等老兄來證明呀。」於是,傳播消息,集合僧、俗四眾,為說最後的法要,叮嚀罷,說偈云:
坐脫立亡,不若水葬;
一省柴燒,二省開壙;
撒手便行,不妨快暢;
誰是知音?船子和尚!
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自己盤坐大盆中,隨著潮水,順流而下。大眾殷勤相送,一路追隨到海濱,直到波濤浩渺,望斷目光,不見師的蹤影。卻又忽然看到他拔了塞子,自己用斗杓舀著水,駛回大盆。大眾圍觀檢視,卻見大盆竟未曾進水。檢視完,又趁著潮水,一盆浩浩,航行而出,高聲唱道:
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
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
歌聲漸遠,笛聲蕭咽。蒼茫水天間,唯見一支鐵笛擲向空中,吞沒而逝─一場生死遊戲。玩得亦莊亦諧,既突梯滑稽,又雄渾蒼茫、凜冽襲人。一名奇異、不世出的「快活烈漢」─以他的反骨反俗,以及「黑色幽默」,睥睨了死亡的場景:無論哪一種死,武裝暴力、鋒刀血刃,或平靜莊園、小鄉無事……他總是游刃自在,為其中的帝王與統御。上馬、下馬,俱是他。也俱由他。死神,僅是他卑微的奴婢與跟班。任何時刻,俱僅能應喏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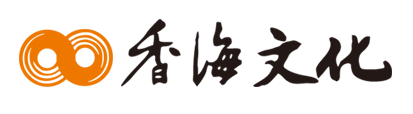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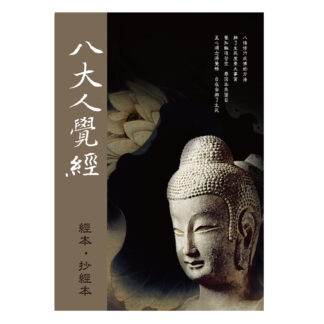

商品評價
目前沒有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