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內容簡介
一本有系統地詮釋禪與音樂的著作
田青教授致力推動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希望更進一步的發揚。好比崑曲、南京雲錦等都是田教授帶領研究,向聯合國申請成功的成果。
田教授所做的一切,在個人,是專業的領域,但這已不只是他小我的成就,而是對於整個社會、國家、民族、人類大我的貢獻。
――星雲大師
水流花謝皆聲色 雲淡風清天籟音
――南懷瑾
禪思悠悠,琴韻悠悠,
禪與音樂的因緣,
也如秋日的湘水一樣,
澄澈深幽。
《禪與樂》是著名學者田青先生的十年力作。作者從佛學、美學、音樂學的各個層面,運用深刻獨到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文筆,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全面梳理了禪與中國音樂的因緣,“發現”了中國傳統音樂中深蘊的禪意,為中國音樂的未來開出一劑良方。
隨書贈送一片CD,內容包含六首作者強力推薦樂曲,帶您進入一個禪樂靈動深邃空靈的意境……
目錄
推薦序 星雲大師
序文
第一章 中國人的宗教觀和音樂觀
一、郭沫若的問題︰中國為何沒有產生宗教?
二、偉大的禮樂之邦
三、中國哲人的音樂思考
第二章 白馬東來
一、兩個偉大文明的相遇
二、禪與禪宗
三、何處無佛?──禪宗影響下的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音樂
第三章 活潑的禪心與流動的音符──禪與音樂的相似性
一、「直指人心」的禪與「不立文字」的音樂
二、公案︰誰能確解?
三、音樂︰一說便錯
第四章 禪風樂韻
一、單旋律中的禪意──「簡約」與「明心見性」
二、「見性成佛」的法門與中國音樂的「韻」
三、簡約之風與古琴減字譜的出現
第五章 禪者︰在山水與音樂之中
一、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大自然
二、文人士大夫的佛教信仰與音樂生活
三、王維與白居易
四、永遠的蘇東坡
五、琴僧──一個特殊的音樂家群體
第六章 禪曲探珠
一、〈普安咒〉與〈那羅法曲〉──琴曲中的佛曲
二、〈江河水〉──是「階級壓迫」還是「有生皆苦」?
三、世界上最慢的音樂──南音
四、一首鮮為人知的偉大樂曲──〈行道章〉
五、生命的鮮活、自由、靈動──潮州箏曲〈行雲流水〉
第七章 中國音樂向何處去
一、西風東漸與國樂凋殘
二、魂兮歸來!──中國音樂的復興之路
後記
作者簡介
音樂學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長期致力於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和宗教音樂的研究,積極推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因力推「原生態」唱法、主張文化多樣性、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而在中國文化界有較大影響。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崑劇古琴研究會會長、中國佛教協會顧問、全國政協委員。著有《中國宗教音樂》、《淨土天音》、《撿起金葉》、佛教音樂的華化》等多部著作。
特別推薦
出版緣起
星雲
我從一九八九年春天第一次返鄉探親以來,認識的、要感謝的朋友很多,除了政府官員、中國佛教協會諸方大德、法師,以及國家宗教局等領導,其中有兩位最為特殊,一位就是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長者,一位就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田青教授。如果說,佛光山在兩岸未通之時,得以宗教先通,乃至後來兩岸文化的交流上有一點點貢獻,其中之一,就是要感謝田青教授的穿針引線。
二○○三年,田青教授熱忱的促成下,成功的邀請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到北京中山堂、上海大劇院演出,讓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佛教音樂,正式登上了大陸的音樂殿堂。這可以說是歷史以來的一大進展與成就。
我常說,佛教的梵唄音樂,都是用來讚詠佛陀,過去只有在寺院的殿堂裡唱給佛祖聽,今天,能走上國家劇院、音樂廳、社教館,唱給「人人是佛」的現前諸佛大眾一起共賞,不是更有意義?這一演出,造成當時社會極大震動。之後,中華文化交流協會、中國佛教協會及國際佛光會共同主辦,由兩岸三地佛教界組成了「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田教授擔任總指揮,分赴澳門、香港、臺灣、美國、加拿大等地,不僅演出反應熱烈,並且取得了極大的回響。
二○一○年五月,承蒙田青教授協助,獲得文化部蔡武部長支持,讓「一筆字」有機會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並且讓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講說「中華文化與和諧社會」。佛陀在二千六百年前建立「六和僧團」,出家人稱「和尚」,就是「以和為尚」,今天胡錦濤總書記提倡「和諧社會」,可以說為中華民族千年萬古的歷史樹立了重要的標竿,讓未來的子子孫孫不再有對立,不再有戰爭。我一介僧侶,在眼睛模糊、老邁之齡,也不禁效法「剖心羅漢」,為兩岸文化的交流、和平的往來、人民的安樂,盡一片心意而戮力以赴,這也要感謝田青教授的因緣成就。
田青教授尤其致力推動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希望更進一步的發揚。好比崑曲、南京雲錦等都是田教授帶領研究,向聯合國申請成功的成果。在二○一○年歲末,歷時一年多織錦的「雲錦袈裟」,在田教授陪同下,由南京雲錦研究所王寶林所長、南京雲錦博物館館長張玉英送給了佛光山、送給了佛陀紀念館,讓全臺灣,乃至全世界來到佛陀紀念館的人士,都可以一睹這老祖先寶貴的智慧遺產。
田教授所做的一切,在個人,是專業的領域,但這已不只是他小我的成就,而是對於整個社會、國家、民族、人類大我的貢獻。如今,田青教授將他歷年來關於佛教音樂的論述,交給我們香海文化來出版,這是我們的榮幸,希望藉此因緣,能喚起海內外中國人對中國佛教音樂的珍惜之情,並為人類歷史留下璀璨的篇章。是為序。
二○一一年七月十七日
於佛光山開山寮
註:此文原為星雲大師為田青先生著作《佛教音樂的華化》所寫,權為序。
弁言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帶著北京佛樂團去德國巴伐利亞參加「世界宗教音樂節」,在許多場演出中,有一場演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所大學的小禮堂,上半場是一個日本音樂家的尺八獨奏,下半場是我們北京佛樂團的節目。在後臺共用的演員休息室,我們團的十幾個團員一邊準備演出的「傢伙」,一邊你一言我一語地聊天。而那個日本音樂家卻在休息室的一個角落默默打坐,他唯一的隨從——他的兒子則默立在側。我們團的一個團員對我說︰「他只有一個人?那肯定演不過我們!」我沒有說話,只是示意他們輕聲,不要打擾那個打坐的日本音樂家。快開演了,那個日本音樂家徐徐起身,他的兒子托著一套繡著族徽的禮服跪在他面前。待他向族徽行禮之後,兒子才侍候他恭敬謹嚴地穿上禮服。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進行的。這儀式感極強的穿衣過程結束後,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眼睛看著地面,輕輕地向舞臺走去。 我讓我的團員們安靜候場,然後繞進觀眾席,在最後一排靜靜坐下。那個日本音樂家跪坐在舞臺中央,依舊低眉看著地面,一言不發。我不知道那靜默究竟有多久,是兩分鐘?還是三分鐘?抑或更長?但我卻深深地感到,他的沉默不是空白,而是一種力量,因為所有的觀眾都似乎感受到了什麼,不知不覺地和他一樣沉浸在靜寂中,大氣不出,好像不是等待一場音樂會,而是在期待著某種重大事件的發生。他終於把尺八放到嘴邊,那聲音,彷彿從遼遠的時間深處傳來,嗚咽著,把一種亙古即在的蒼涼和溫暖送到觀眾的心中。他一個人,一隻尺八──一隻從中國傳過去、但在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失傳而只保留在南音音樂裡、被閩南人稱作洞簫的樂器──不間斷地演奏了半場,沒有第二個人,沒有任何其他的陪襯和幫助。當他起立行禮的時候,觀眾才彷彿從他音樂的魔法中驚醒,用長時間的掌聲向他們心目中的東方致敬。
後半場是我們團演奏的北京佛樂,十幾個團員,除了來自北京廣化寺的兩個僧人外,都是北京民間佛樂著名傳人張廣泉的弟子,能夠嫺熟地演奏從智化寺京音樂到被稱為「怯音樂」的北京民間佛曲。他們的樂器,完全是正宗的北方佛教音樂的正統樂器──笙、管、笛加雲鑼,還有鼓、鐃鈸、鐺子、木魚等法器,這是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數十年「破除迷信」教育和 「文革」浩劫之後少數僅存的尚可演奏佛教音樂的隊伍。他們的演奏,當然也獲得了歐洲觀眾的讚賞和歡迎。我不能說那天的演出是上半場更成功還是下半場更成功,因為兩種音樂「各美其美」,無法比較。但是那天演出結束後晚宴上一個歐洲音樂學者的問話,卻令我感到一種羞愧和困惑。而正是由於這個羞愧和困惑,促使我寫下了讀者正在讀的這本書。他說︰「在日本的尺八音樂中,我聽到了禪意。而在中國的佛教音樂中,我聽到的卻和我在中國民間音樂中聽到的一樣,嗯,好聽,但是有點吵。請問你,這是為什麼?」
我當時給他講了中國佛教「華化」的過程和佛教與中國民眾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繫,講了明清之後中國興起「人間佛教」的情況,講了中國佛教音樂的功能和場合,講了中國普通民眾的審美習慣與民間音樂對佛教音樂的影響,我更強烈地向他指明,無論是禪還是尺八,其故鄉都是中國!但是,我卻從他的眼睛裡,讀到了一種被禮貌掩蓋著的他自己的價值判斷。
其後,我不斷地被這個問題困擾︰為什麼中國現存的傳統音樂(包括佛教音樂和道教音樂)裡,我們似乎感受不到禪意?感受不到這個曾經深深影響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深邃博大的東方智慧和精神?是中國音樂與禪無緣,還是我們的考察不夠深入?尤其是近年來,當研究禪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已經成為一門顯學,乃至禪與中國文學、禪與中國詩歌、禪與中國繪畫等等的著作大量出版的時候,禪與中國音樂的關係,卻至今鮮有論者。這很奇怪,也不應該。因為無論就其形而上的層面而言,還是就其形而下的層面而言,都再也沒有一種藝術門類像音樂一樣與禪有著如此眾多的相似性了。
禪與中國音樂的密切關係、中國傳統音樂中所深蘊著的禪意,以及禪和禪宗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音樂的事實,從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當今中國音樂發展中暴露出的主要問題,是背離了中國傳統音樂的本性和傳統,丟棄了中國傳統音樂中曾經蘊含著的禪意,盲目、全面地照搬西方音樂的一切。只有在透澈瞭解中國音樂與禪近似的本質之後,只有在重新憶起禪和禪宗曾經深刻影響中國音樂的發展歷程之後,我們才能突破「弱勢文化」的困境,找回中國音樂獨特的意境。而只有深具禪意的音樂,才能在國際樂壇上彰顯華夏獨特的樂風。
唐時,有一位詩人有幸在僧院中聽琴,聽琴之後,他吟出了這樣四句詩︰
禪思何妨在玉琴,
真僧不見聽時心。
離聲怨調秋堂夕,
雲向蒼梧湘水深。
禪思悠悠,琴韻悠悠,禪與音樂的因緣,也如秋日的湘水一樣,澄澈深幽。
書摘
第三章、 活潑的禪心與流動的音符──禪與音樂的相似性
一、「直指人心」的禪與「不立文字」的音樂
假如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的一瞬間便開始了禪「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傳承,那麼,從某個原始人第一次僅僅為了高興而撥動弓弦的一瞬間開始,音樂,便也走上了與語言並行但各自獨立發展的道路。 中國民間過去曾有一句頗有禪意的老話︰「人生識字糊塗始」,的確道出了部分真理。語言文字,作為世間文化和知識的載體,作為人類交往的工具和手段,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有著固有的局限性。釋迦說法四十九年,臨終時稱自己「未說一字」;《老子》「五千言」,第一句話也是︰「道可道,非常道」,認為世上凡是可說的道理,可以用語言表達的道理,都不是真正、長久的道理。對人類語言的局限性以及對終極真理的非語言性的清醒認識,應該是東方古典哲學對人類認識史的一個重大貢獻。
在禪宗看來,所有修行的門徑、方法、過程,以及最終的目的,統統可以概括為四個字︰明心見性。雖然「見性」是目的,「明心」是手段,但禪宗最看重的是心,是心的澄靜和解脫。中國禪宗「二祖」慧可悟道前寧可跪雪斷臂也要「解脫」的最大煩腦便是「吾心不寧」,而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乞師與安」――求師為其安心。菩提達摩為慧可開悟,使慧可「立地成佛」的一句話,也是這五個字︰「與汝安心竟」。但是,恰恰在「明心見性」的過程中,文字常常成為「心」的羈絆和障礙。有一個曾被廣泛引用的禪宗公案說︰一個學者來向禪師學禪,禪師為他倒茶時有意一邊說話一邊倒,茶杯滿了,禪師還在繼續倒,學者只好提醒他說︰「滿了!滿了!」而實際上,禪師正是要用這個行動提醒學者,他自己就像這個裝滿了水的杯子,如果不把已裝滿腦袋的舊思想、舊觀念、舊思維方式統統倒掉,是無法再灌進新東西的。這位學者所長的語言、文字,在學禪的路上,卻可能是他「文字障」。
音樂與禪一樣,在本質上便具有「反文字性」,一切企圖用語言來「描述」音樂的嘗試,都是徒勞的。在音樂欣賞領域裡,人們最常犯的一個概念錯誤,便是用「聽懂聽不懂」來表示對音樂欣賞的結果。音樂不是文字和概念,沒有什麼「懂」與「不懂」,而只有「喜歡」與「不喜歡」以及其他類似的感覺。正像禪強調體悟和心靈的感受一樣,音樂需要的也僅僅是感受,是個人的、不可替代的感受。而且,這種感受從根本上講,也是無法用語言和文字表達的,是「不可言傳」的。人們用語言和文字表達的東西,充其量,也只是你個人感受(注意︰是「你的」,而不是「音樂的」)的文字化。即使是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千古名句,所描寫的也只是音樂在詩人心中所引起的聯想,而不是感受的全部,更不是音樂本身。禪宗有一句真正了悟的話,叫「一說便錯」。對音樂欣賞而言,其實也是「一說便錯」。奧地利著名的音樂美學家漢斯利克(一八二五-一九〇四)有一個和他本人同樣著名的命題︰「音樂的內容」,僅僅是「樂音的運動形式」而已。現在,愈來愈多的音樂學家們認為這個過去被譏評為「形式主義」的觀點,有著深刻的道理。其實,西方的詩人早就說過︰「話語停止的地方,便是音樂的開始。」 而東方的哲人在這個問題上說得更透澈︰「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認為好的、善的語言不如好的、善的音樂更容易深入人心,在道德標準第一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並強調了音樂對語言的超越。
雖然禪與音樂都是一種對語言的超越,但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釋迦傳教,從來是「應機說法」。對號稱「頭陀第一」的迦葉,當然可以「以心傳心」;對芸芸眾生,則只能明知不可說而說之, 即所謂「 不說之說」。禪宗的公案語錄、棒喝機鋒,都是語言的變形和替代品,其目的,無非是打破你舊的思維定勢,令你豁然開悟。與此同理,在音樂美學中的「音樂形象」一詞,也是一個勉強為之、約定俗成的概念。有趣的是,音樂形象的模糊性、多義性,與禪宗公案的不可確解,也有著驚人的相似。
佛教把一種透澈的智慧稱為「般若」,這種建立在「緣起性空」的理論基礎上,超越了世俗認識與事物表面現象,直接達到事物的本來面目、把握諸法真如實際的智慧,可以稱作「超越的智慧」。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智慧的運用過程和達到的結果也是不可言說的。音樂與此相似,它通過人的感官讓人直接體會到事物的本質。一些真正被音樂打動的人常常在音樂中體會到某種超理性的東西,但是他卻無法準確地傳達給其他人。那種在樂聲中「砰然心動」、似有所得的感覺,極像禪宗所說的「頓悟」――在刹那間豁然貫通、洞若觀火。人們在此時從音樂中體味到的東西,也類似「般若」――它穿透了事物周圍的一切,也穿透了事物的表像,直達事物的本質,直接洞悉生命的真實意義和世界的本來面目。 第六禪曲探珠
一、〈普安咒〉與〈那羅法曲〉──琴曲中的佛曲
滄海桑田,曾經在中國人生活中長期存在並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心靈的佛曲和充滿禪意的樂曲漸漸被現代人冷落了。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悲哀。在這一章裡,我從大海般浩瀚的佛曲禪音中撈起幾顆珍珠獻給讀者,這裡,有長期流傳在鄉間的民間佛曲,也有充滿禪意的古老音樂。
雖然我們常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是儒、釋、道三家,雖然我們講了這麼多歷代琴僧的事蹟,但在現存於世的上千首琴曲中,卻極少反映佛教內容的琴曲,真正流傳於世並為人所熟知的佛教琴曲,似乎只有〈普安咒〉一曲。
〈普安咒〉又名〈釋談章〉,樂譜最早見於明末的《三教同聲》琴譜(一五九二年)。在這本明代的曲譜中,曲名為〈釋談章〉,但譜旁配有〈普安咒〉的經文,因此人們便認為這兩個名字指的是同一首樂曲。
咒語也叫真言,即真實不虛的語言的意思。梵語為mantra,音譯「曼怛羅」、「曼荼羅」,「陀羅尼」。也稱咒、明、神咒、密言、密語、密號。在佛教密宗中,屬於「三密」中的「語密」。漢傳佛教的習慣,對真言均不作翻譯,而直接運用原語的音譯,認為念唱或書寫、觀想其聲音、文字,即可得到與真言相應的功德。按照《楞嚴經》的說法,修行證得「八地菩薩」以上果位的菩薩即可自說咒語 。佛教傳入中國逾兩千多年,高僧大德數不勝數,但創有自己咒語的只有普安(普庵)禪師一人。換句話說,〈普安咒〉,是中國僧人對佛教真言的唯一貢獻。
普庵禪師,南宋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年)生於江西袁州宜春,俗姓余,字肅印,為禪宗臨濟第十三代法嗣。肅印二十七歲出家,二十八歲受甘露大戒,後訪溈山,禮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據說,印肅禪師曾問牧庵禪師︰「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庵禪師便豎起拂子示之。印肅禪師一見,恍然有省。印肅求法心誠,精進用功,「脅不至席者十二餘年。」一日,研讀《華嚴合論》,讀至「達本忘情,知心體合」句時,豁然大悟,遂作偈曰︰
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臺。
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
據說,悟道之後的普庵禪師神通廣大,祈福攘災,治病救人,莫不靈驗,頗受時人敬仰。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年),印肅臨終前書一偈於方丈西壁︰
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橫。
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
書罷,跏趺而逝,時年五十五歲,留有《普庵印肅禪師語錄》三卷傳世。明永樂年間,成祖因其「萬行圓融,六通具足。端嚴自在,變化無方。誓覺悟於群迷,普利益於庶類」而賜諡號︰「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
《禪門日誦》中,在〈普庵大德禪師釋談章神咒〉題目下標有一行小字︰「此咒三迴九轉,勿致紊亂。朔望當念,餘日或減。」普庵咒在佛教徒長期的誦念中,以其滔滔不絕、素湍迴流般的音聲和規整、往覆的節奏,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旋律,其對聽者的心理影響,大大超過了普通的音樂。佛教徒們相信,念誦此咒語,可以蕩妖除穢、身心平安。由於此咒念誦時鮮明的節奏感和音樂性,為其走出佛門發展成完整的器樂曲提供了可能。而由於此曲獨一無二的宗教性和藝術性,此曲及其變體、以及同名異曲廣泛存在於中國傳統音樂的許多領域,在五臺山寺廟音樂、弦索樂、琵琶曲、昆曲、南音中,都可以見到〈普安咒〉的傳承。
目前已知最早刊載琴曲〈普庵咒〉的《三教同聲》琴譜,係明萬歷年間張德新編訂,成書於明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張德新字嘉甫,又號賓桐,新安人。《歷代琴人傳》記載其︰「善琴,能取各書譜入絲桐。」鐵耕道者鄭邦福曾為該琴譜作序,序曰︰ 新安張賓桐氏,素精琴理。凡可持誦諷詠之者,悉能被之於弦,以清入耳。余為比部時,見其〈釋談章〉譜,按而習之,如入梵宮,聞眾僧咒,既心異之。越二年余以入賀抵都,又見其以《大學》、《清靜》二聖經,譜而按之,與前音配,吁!亦奇矣。夫賓桐氏欲聯三教以同聲,何其所志之弘也。乃忽獻疑於予曰︰「吾儒與道家者流,其習於琴久矣。乃佛氏以音聲色相為邪道,則釋談章之譜得無悖於本旨乎?」予曰︰「不然,琴之設,無非禁人之不正,以歸於正,咒為佛祕密語,雖不可以文字解,而其為教,亦欲攝群魔以歸之正,此其意旨原不謬於聖人,況道流乎?人患不達先王作樂之本耳,達其本則觸處泠然無性,非正性之具,即佛氏之風水樹鳥皆能說法,梵音潮音皆屬妙音。於琴理又何礙也?」賓桐氏遂釋然領悟,並以此語並之簡端。余嘿然無言。
在琴曲中,除《三教同聲》琴譜之外,其他許多琴譜如《伯牙心法》、《太音希聲》、《太古正音》、《理性元雅》、《陶氏琴譜》、《琴學心聲》、《德音堂琴譜》、《琴瑟譜》、《五知齋琴譜》、《琴學入門》、《古音正宗》、《臥雲樓琴譜》、《治心齋琴學練要》、《琴劍合譜》、《蘭川館譜》、《琴香堂琴譜》、《研露樓琴譜》、《自遠堂琴譜》、《晨露軒琴譜》、《峰抱樓琴譜》、《琴學端》、《張鞠川琴譜》、《稚雲琴譜》、《蕉庵琴譜》、《天聞閣琴譜》、《梅庵琴譜》等近四十種琴譜中都收錄了〈普庵咒〉(或〈釋談章〉)一曲。總括所有琴譜,可以看到琴曲〈普安咒〉大體存在三種不同的形式︰配以咒文誦唱的二十一段〈釋談章〉,配以咒文誦唱的十三段〈普庵咒〉,以及脫卻咒語,純器樂化的琴曲〈普庵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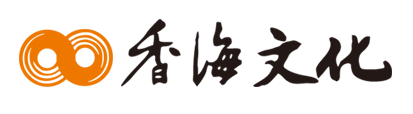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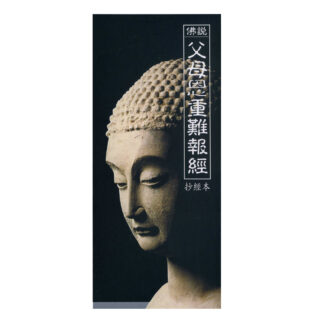


商品評價
目前沒有評價。